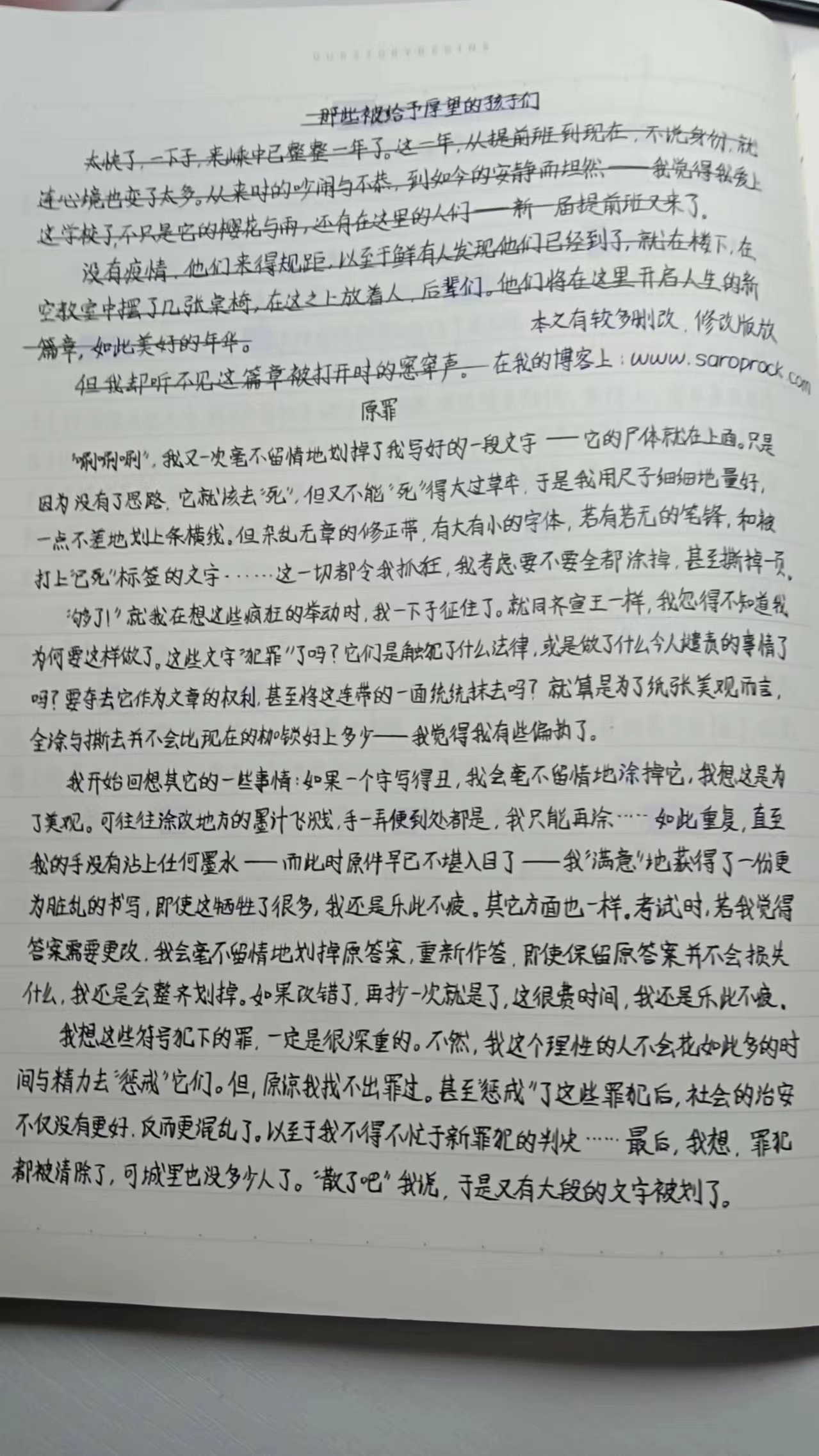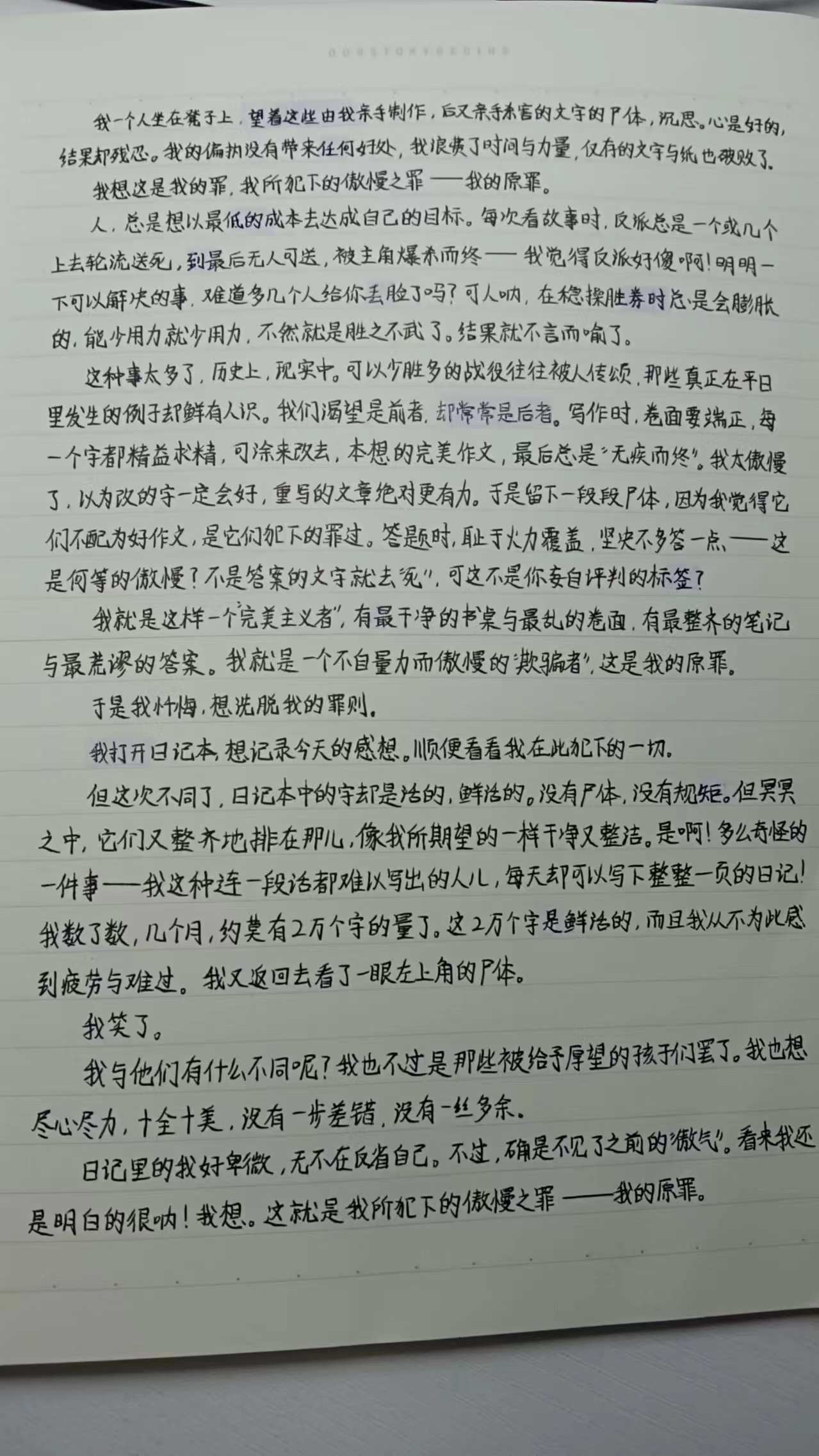原罪
太快了,一下子来嵊中已整整一年了。这一年,从提前班到现在,不说身份,就连心境也变了太多。从来时的吵闹与不恭,到如今的安静而坦然——我觉得我爱上这学校了,不只是它的樱花与雨,还有在这里的人们——新一届提前班又来了。
没有疫情,他们来得规距,以至于鲜有人发现他们已经到了,就在楼下,在空教室中摆了几张桌椅,在这之上放着人,后辈们。他们将在这里开启人生的新篇章,如此美好的年华。
但我却听不见这篇章被打开时的窸窣声。
“唰唰唰”,我又一次毫不留情地划掉了我写好的一段文字——它的尸体就在上面。只是因为没有了思路,它就该去“死”,但又不能“死”得太过草率,于是我用尺子细细地量好,一点不差地划上条横线。但杂乱无章的修正带,有大有小的字体,若有若无的笔锋,和被打上“已死”标签的文字……这一切都令我抓狂,我又考虑要不要全都涂掉,甚至撕掉一页
“够了!”就我在想这些疯狂的举动时,我一下子征住了。就同齐宣王一样,我忽得不知道我为何要这样做了。这些文字“犯罪”了吗?它们是触犯了什么法律,或是做了什么令人谴责的事情了吗?就要夺去它作为文章的权利,甚至将这连带的一面统统抹去吗?就算是为了纸张的美观而言,全涂与撕去并不会比现在的枷锁好上多少——我觉得我有些偏执了。
我开始回想其它的一些事情:如果一个字写得丑,我会毫不留情地涂掉它,想来这是为了美观。可涂改地方的墨汁往往肆意飞溅,手一碰便到处都是。如此,脏乱的地方更多了,我只能再涂……如此重复,直至我的手没有沾上任何墨水——而此时原件早已不堪入目了——我“满意”地获得了一份更为脏乱的书写,即使这牺牲了很多,我还是乐此不疲;其它方面也一样,考试时,若我觉得答案需要更改,便会毫不留情地划掉原答案,重新作答,即使保留原答案并不会损失什么——甚至可以骗一点分数,我还是会整齐划掉。如果改错了,那再抄一次就是了,这很费时间,我还是乐此不疲。我想这些文字犯下的罪,一定是很深重的,不然,我这个理性的人不会花如此多的时间与精力去“惩戒”它们。但,原谅我找不出罪过。甚至“惩戒”了这些罪犯后,社会的治安不仅没有更好,反而更混乱了,以至于我不得不忙于新罪犯的判决……最后,罪犯都被清除了,可也没多少人了。“散了吧”我说,于是仅存的文字也被抹去了。
我一个人坐在凳子上,望着这些由我亲手制作,后又亲手杀害的文字的尸体,沉思。心是好的,结果却残忍。我的偏执没有带来任何好处,我浪费了时间与精力,仅有的文字与纸也破败了。
于是,我想,这是我的罪,我所犯下的傲慢之罪——我的原罪。
人,总是想以最低的成本去达成自己的目标。每次看故事时,那些反派总是一个或几个上去轮流送死,直到最后无人可送,被主角爆杀而终——我觉得这些反派好傻啊!明明一下可以解决的事,难道多几个人给你丢脸了吗?可人呐,自以为稳操胜券时总是会膨胀的,能少用力就少用力,不然就是胜之不武、丢脸了,但结果就不言而喻了。
可当我们嘲笑这些反派时,却没有想过,这种事情其实太多了:历史上、现实中,还包括现在的我。但以少胜多的战役往往被人传颂,那些真正在平日里发生的例子却鲜有人识。我们渴望是前者,却常常是后者。写作时,卷面要端正,每一个字都要精益求精,可涂来改去,本想的完美作文,最后总是“无疾而终”。我太傲慢了,明明知道字改与不改,段落删与不删都没有区别……却自以为改的字一定会好,重写的文章绝对更加有力。于是留下一段段尸体,只是因为我觉得它们不配为好作文,它们就应该被抹去;答题时,明明知道答案划与不划都不会影响评分……却耻于火力覆盖,坚决不多答一点——这又是何等的傲慢?不是“答案”的文字就去“死”,可这“答案”难道不是你妄自评判的标签?
我就是这样一个虚假的“完美主义者”,有最干净的书桌与最乱的卷面,有最整齐的笔记与最荒谬的答案。我就是一个不自量力而傲慢的“欺骗者”,这是我的原罪。
于是我忏悔,想洗脱我的罪则。
我打开日记本,想记录今天的感想。顺便看看我在此曾犯下的一切。
但这次不同了,日记本中的字却是活的、鲜话的。没有尸体,也没有规矩。但冥冥之中,它们又整齐地排在那儿,像我所期望的一样干净又整洁。是啊!多么奇怪的一件事——我这种连一段话都难以写出的人儿,每天却可以写下整整一页的日记来!我数了数,几个月,约莫有两万个字的量了。这两万个字是真正活着的,而且我从不为此感到疲劳与难过。我又返回去看了一眼左上角的尸体……
我笑了。
我与他们有什么不同呢?我也不过是那些被给予厚望的孩子们罢了。我也想尽心尽力,十全十美,没有一步差错,没有一丝多余。
日记里的我好卑微,无不在反省自己,不过,确是不见了之前的傲气。看来我还是明白的很呐!我想。这就是我所犯下的傲慢之罪——我的原罪。